
| 怎樣利用《和平》祈禱? |
| 《和平》首頁 |
| 本月份《和平》目錄 |
| 訂閱《和平》 |
| 二零一六年 五月《和平》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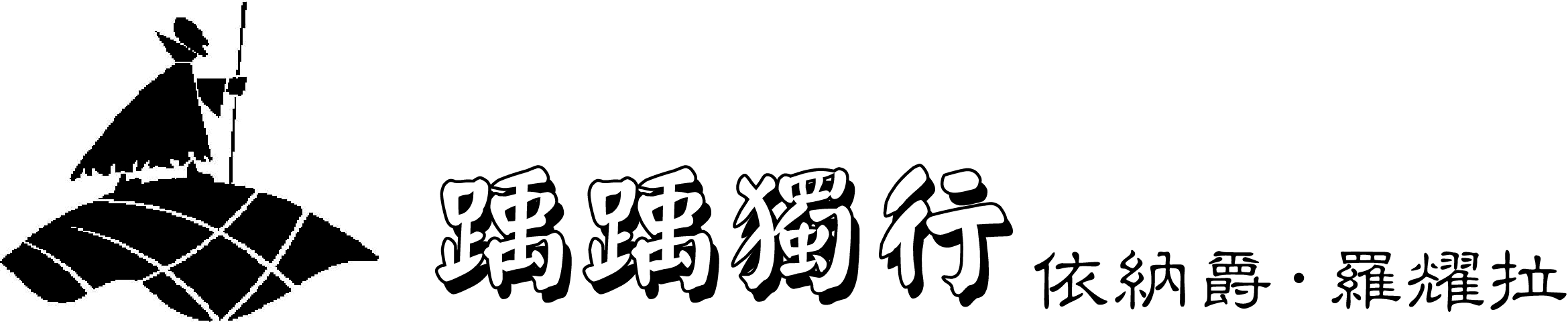 (譯自高伯仁神父共七十章的Alone and on Foot) (續前) 第六十九章:默默改革 別出心裁 依納爵生活在一個混亂的時代,一個充滿激情、英雄豪氣和分裂的時代,也是一個許多男女在西方文明史上留下芳名的歷史時代。年輕時的依納爵與其他歐洲人沒有什麼分別;但他「停下來思考」之後,開始變得與眾不同,別出心裁,甚至是獨樹一幟。這帶領他跨越了一個大多數人從未跨越的無形邊界。接著他開始走他的路,其中一部分是很多前人走過的舊路,但亦同時是他個人的新路線,就像在他家鄉的山坡,由走獸走出、微細而不被察覺的路徑。盲目相信未來,懷著另一個亞巴郎的信德,他離開家鄉,踏上了這條不確定但已下定決心要走的小路。他不知道這小路會把他帶到哪裏,只知順從內心的召喚。他相信「有一位」在帶領。 轉化人心 依納爵並非像許多文藝復興時期的人物那樣,嘗試設計自己的一套體系。《神操》的重點在於個人的更新,而不是改革教會的教義或管理制度。他努力淨化教會,而不是將她推翻,他喜歡去肯定和勸告,不喜歡鬥爭、反抗或強加於人。他認為個人經驗和實際生活比書本知識或全世界的理念都重要;世界的問題需要根治,光有知識亦無補於事。他關心讀聖經者的內心傾向,多於關心他的學問;他喜歡在路邊給人講授教理。他既是同伴亦是導師,既慷慨大方亦嚴厲要求,一絲不苟,敏銳體貼。他不是沒有敵人,但他不會讓仇恨攻佔他的心,他不會怨恨那些曾迫害過他、虛偽和官方的基督徒。基本上,他不是要反對任何人或任何事。反之,他極樂意幫助人、服務人、提醒人和釋放人,不是用美麗的理論或誘人的計劃,而是提出簡單實際的問題:「我應該做什麼?」這一問要求人作出決定、許下承諾。 「我應該做什麼?」 在一五二一至二二年間,依納爵在羅耀拉堡編織夢想,路德和伊拉斯謨則分別在華爾特堡和魯汶編織他們的夢。三人都領略過作邊緣人的滋味,每人都在牽起一場截然不同的叛亂,都在反對當時基督宗教的虛浮。依納爵說:「當今的基督徒虛有其名」;伊拉斯謨或路德也會說同樣的話。三人都深深感受到教會陷入的混亂,但依納爵的回應既不是批評,也不是啜泣,卻體現了一種高雅莊重的氣慨和男兒風範。高雅莊重,因為人不會把家人的髒衣服擺出來,他不會把羅耀拉家族或他更大的家庭、教會的髒衣服示人;男兒風範,因為真正的男子漢不應該為髒衣服哭泣,也不應該把它丟在一邊,而是去清洗它。換句話說,依納爵相信,他應以行動補救教會的狀況。他先從自己開始,身體力行;之後,是他能夠接觸到的人;最後,伸展至能觸及的時空與地域。這空間永遠比我們想像中或能看見的大,不過要求於我們的,只是懂得怎樣去面對每個人或每種情況。重要的是行動。依納爵注視永恆,努力工作,但他所做的,如同全人類的努力一樣,難免受歷史局限。 天主的人 依納爵沒空花時間在我們認為重要的消遣上:他每時每刻都忙碌不已。各種在發生的情況和事件,他都斟酌一番。反覆思考過問題的正反兩面之後,他要考慮該作什麼,因為聖神的聲音尚未十分清晰。同一位聖神曾經藉著騾子隨意的腳步引導了他,也藉著團體的意願、威尼斯船隻的意外帶領了他。起初,他的言詞未經打磨,尚未擦亮,不是大聲疾呼宣講,而是給人的靈魂耳語。透過他靜靜地散發的感染力,他贏得人棄惡從善。「一把火炬點燃另一把」。 依納爵不為自己尋求什麼,但為自己所作的服務尋求一切,因為縱使我們不曾渴望擁有什麼,卻渴望所愛的人能夠擁有。依納爵謙遜地繼續他的旅程,沒作非分的計劃、承諾或手段 ──「我們一路上跌跌碰碰」。此時,已有許多「準備好迎接一切」,甚至準備好接受迫害的人,跟隨他。在他死後六個月,一位嚴規熙篤會隱修士列了一張起初耶穌會士遭到攻擊的罪狀清單:「人們說他們起革命;他們傲慢地把耶穌的聖名用在自己身上;他們不穿修道人的會衣;不詠唱教會訂定的時辰日課。還有一些人批評他們太過投入民眾,也有人抱怨說他們在短時間內人數增長得太快」。然後,他給予依納爵這個結論:「天主的那個小人物有耐心去忍受這一切」。 臨近尾聲,以此總結「一個貧窮的基督徒的探索之旅」,不失是個簡潔的定義。依納爵所走的路,是許多其他道路中的一條,他穿越埃塞俄比亞、巴西、日本和德國;進到剛迪亞公爵的公署和葡萄牙國王若望三世的宮廷,踏進許多大學的講壇和許多學院的門房,也走進羅馬道路聖母堂的廚房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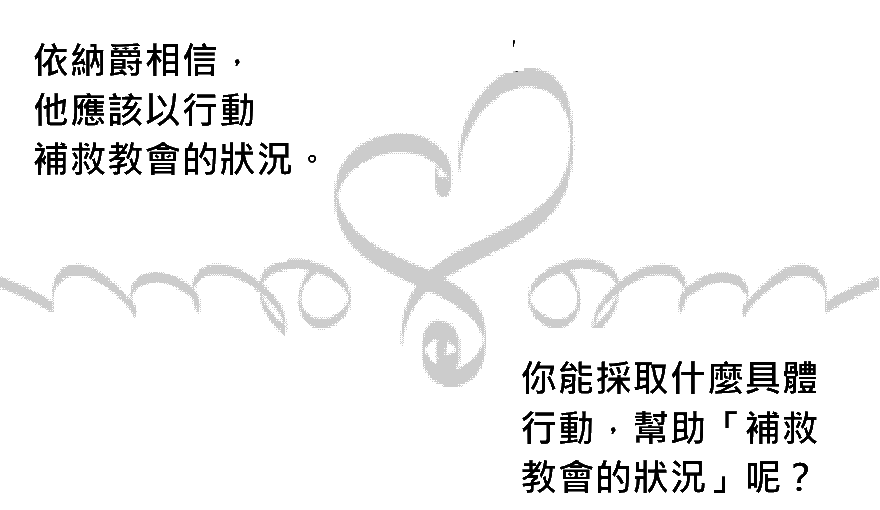 (待續)
© Copyright Shalom 2016. All rights reserved.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