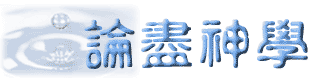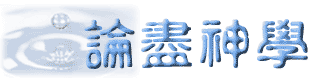|
mitrophanes
|
Posted -
2004/9/20 下午 09:09:19
|
|
|
聖者的傳統
(The Customs of the Noble Ones)
原文出處:【Access to Insight】
原文:譚尼沙羅比丘(Thanissaro Bhikkhu)
中文翻譯者: Shepherd
綜觀歷史,佛教在文化上,一直是一股強大的教化力量。譬如說,佛教中的業力說(karma)---認為所有出於意欲的行為,都會帶來果報---所教導的關於道德與慈悲的訓示,影響了許多社會。但是在更深一層的意義來說,佛教早已跨越所謂世間文明(civilization)與大自然(wilderness)之間的界線。佛陀本身在森林開悟,在森林開始他第一次的教說,最後也在森林逝世。(佛陀在未成道時)有一次他醒悟到:為了具備證悟真理的特質,必須捨棄所有身外之物,獨自進入深林之中。這是他自覺於正法的關鍵所在。這些心靈上的特質,包括了一顆保持彈性、決志、警覺的心,誠實、謹慎的人格,處於孤獨時的堅定不移,面對危境時的勇氣與機智,以及對於同為森林修行者的慈愛與尊敬等。就是這些特質塑造了法的根本傳統(home culture)。
有的時候,當佛教向四方傳播並適應各種不同的風土民情時,一些有識之士認為在這樣的歷程中,反而來自法(dhamma)的訊息被稀釋了。所以他們回歸大自然,試著要回復那被忘失已久的「根本傳統」(home culture)。很多森林傳統(wilderness tradition)直至今日都還存在,特別是在斯里蘭卡與東南亞等上座部佛教國家的叢林中被實踐著。在那裡,頭陀僧們繼續在已遭到大量砍伐、碩果僅存的雨林裡遊歷。他們之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中致力最終的覺悟,是因為佛陀自己就是這樣走過來的。在這些主張回歸叢林的不同傳承之中,吸引最多西方學習者的目光,甚至已經在西方世界生根的,是泰國的Kammatthana森林傳統。(譯按:kammatthana,即「業處」之巴利文。由於廣為人知,現在kammatthana也成為由阿迦曼、阿迦索所建立的森林傳統之代稱。)
Kammatthana森林傳統是由阿迦曼•布利達陀(Ajaan Mun Bhuridatto)在二十世紀早期所建立的。阿迦曼的教法強調隱遁與嚴格的修行,他忠實地遵守比丘律制,並奉持十三頭陀行的儀軌,例如外出托缽,穿碎布衣,住止在曠野裡,與一日一食等等。為了尋找適合遺世獨立的修行處所,阿迦曼在泰國與寮國境內的曠野裡不定游方,而這樣也能盡量避免那些定居於寺院時所需負擔的眾多雜務; 他選擇以這樣的方式,以便能日夜精進於禪定的修習。儘管阿迦曼偏好出離隱遁的生活,這依然吸引了許多願意忍受刻苦叢林生活的比丘追隨他,並成為他的弟子。
然而阿迦曼也招致了反對者的批評。他們認為,阿迦曼並不遵循泰國的佛教傳統。對此,他的回應通常是: 「關於你們所宣稱的,要人們歸化特定時地條件下所孕育出的傳統,對此,我並沒有多大興趣----如果,你們所說的『傳統』,是從人們的種種的貪、瞋、痴所匯集而成的話。」事實上,他更樂於尋找並實踐「法」的「根本傳統」(home culture),或稱之為聖者的傳統(the customs of the noble ones)---最初,就是因為法的修習,使得佛陀與他的阿羅漢弟子得以覺悟。而所謂的「聖者的傳統」,我們可由佛陀本身的一個故事了解的更清楚。佛陀成道後不久,他回到離開六年的家鄉,試著將自己所發現的法(dhamma),傳達給他的家人。佛陀在城外的森林的待過一夜後,於日出時分入城托缽乞食。這時他的父親淨飯王看到了,卻馬上走上前斥責他。「真可恥啊!」淨飯王說:「在我們的家族裡,從來沒有人像你這樣乞討的!這簡直違反了我們家族的傳統!」
「親愛的國王,」佛陀說,「現在的我,已經不再屬於家族的一員了;取而代之的,我是聖者們的一份子。他們的傳統,才是我所樂於遵循的。」
阿迦曼奉獻生命大部份的精力,致力於追溯古聖道足跡。生於一八七○年,他是住在泰國東北烏邦省(Ubon)一名農夫的兒子,然後一八九二年在烏邦省的首府正式剃度為比丘。在他出家當時,泰國佛教約可粗略分為兩種類型。首先第一種可稱為泰國的傳統型佛教(Customary Buddhism)。它們有許多地方習俗與儀式經由師徒相承,幾百年來一代代傳了下來,但是其中關於巴利經典的教法,比重卻反而相當有限(如果還有的話)。這樣的佛教傳統認為,僧侶應該永久長住於村莊的寺院裡,為村民提供醫藥服務,甚至從事算命占卜的工作。僧侶們的紀律漸趨鬆弛毀敗。偶爾僧侶們會出走,實踐他們稱為「頭陀行」(dhutanga)的宗教性行腳,然而事實上,那與正統的頭陀行大相逕庭。他們所謂的頭陀行應該是為了抒發長期久住於一處的煩悶與壓力,而比較像是一種自我放逐。甚至僧侶與在家俗人的修習方向,已偏離了巴利經典所教導的,那平和、寧靜的特質與其偉大洞見所指示的道路。他們的修習方式可稱為咒術(vichaa aakhom, or incantation knowledge),包含帶有薩滿(shamanistic)特質的入教儀式與祝禱文,其目的是為了祈求庇護保祐與獲得不可思議的超人能力。他們很少提及涅槃,但如果有的話,那也只是在儀式中,用來指陳那些無可名狀的的神祕力量罷了。
在阿迦曼剃度當時,另一種可見的佛教型式可稱為改革型的佛教(Reform Buddhism),一八二○年由王子孟庫所創立(他之後登基為泰王拉瑪四世),它以巴利經典的教法為其基本立場。孟庫王子在登基前已經當了二十七年的僧人,在他早期的僧侶生涯裡,每當他經典讀得越多也懂得越多時,與舉目所見的佛教現況作一比較,就更加沮喪不樂。所以他決定在蒙族(Mons)重新剃度---蒙族是一個居住在泰緬邊界的種族,而他們有幾個村落位於一條流經曼谷河流的沿岸---並在蒙族僧侶的指導下學習律藏與正統的頭陀行儀軌。稍後他的哥哥拉瑪三世,相當不滿孟庫以一個王室成員之身,竟會走進一個少數種族的圈子裡去; 因此,拉瑪三世為這位王子比丘建了一座寺院,就在靠近曼谷一側的河岸。在那裡,孟庫吸引了一群為數不多但有相同志向的僧眾與在家居士,法宗派運動(Thammayut法宗派,意指奉行「法」的教派)就因此誕生了。
在早期發展時,法宗派運動還沒有任何正式的組織成形。它宣揚僧侶們應該致力研讀巴利經典,重視戒律,奉持頭陀行; 主張對佛法採理性主義式(rationalist)的闡釋,也曾經嘗試使經典中的禪修技巧再次重現,比如說對佛隨念(譯注:六念法之一)及對身體的專精思惟。然而,在此改革運動中的追隨者之中,竟沒有一個人能證明這些記載在巴利經典的教誨,是否真能導向最終的覺悟。至於孟庫本身也相信,通往涅槃之路於世間已不再開敞,不過他覺得若能重現某些早期佛教的實踐方式,僅管它們是比較偏向外在形式的,至少還是能帶來許多好處的。最後他正式發起了菩薩誓願,期望今生所有功德,都能轉為成佛之道的資糧,而他的許多弟子也宣誓,希望能成為未來佛陀的弟子。
在一八五一年兄長拉瑪三世去世之後,孟庫還俗並繼位成為拉瑪四世,當時他原可以一國君主之權威,把他的改革理念加諸於全體的泰國僧侶身上,然而他並沒有選擇這麼做。他只是在草木不驚的情形下,悄悄資助了首都曼谷乃至各省的法宗派寺院成立---差不多就在阿迦曼的時代---那時烏邦省已有不少的法宗派寺院成立了。
傳統型的佛教難以使阿迦曼滿意,所以他選擇加入了法宗派,由一位孟庫王子的弟子擔仼他的教授師。在法宗派的體制下,必須以學業成就或行政能力做為晉級的考量,然而和同時間加入法宗派的同儕不同的是,他對於提升社會階級的種種機會,實在提不起什麼興趣。相反地,每當憶及舊時鄉間田野的在家生活,就喚起了他對這毫無目的、生老病死一再循環的怖畏;他唯一的目標,就是脫離這生生滅滅永無止境的大圈子。考量的結果,他離開了教授師的寺院,離開了這不乏博學多聞者的環境,然後親近一位名叫阿迦索•康塔悉洛(Ajaan Sao Kantasilo, 1861-1941)的老師,在城鎮外圍的一座小寺院修習。
阿迦索在法宗派的僧侶中算是相當奇特的一位,因為他一向沒有取得學位的興趣,而致力於禪定的修習。阿迦索以嚴格的紀律與經典傳授的禪修方法教導阿迦曼,而且要他在種種充滿危險的環境求生存,體會身處曠野帶來的無比孤寂。阿迦索並不能保證這樣的修習會達到涅槃,但他相信大方向是正確的。
在與阿迦索同行幾年後,阿迦曼支身離去,要另外尋找能確實指點滅苦之道的明師。他的探索持續了幾乎有二十年之久,他的遊歷範圍從寮國、泰國中部、一直到緬甸,此間遭遇到無數的困難,但卻從未能發現他所要找尋的好老師。漸漸地他明白,其實應該要追尋佛陀的腳步,學習以大自然為師,不要屈服於世間諸法的本質---就是輪迴本身---之後粉碎無明,親證超越一切世間思惟的真實知見。另一方面,他知道如果想要找到出離老、病、死的道路,他必須要時時審視所處的週遭環境,學習這老、病、死是如此怵目驚心、卻又不斷上演的一項事實。同時,和其他森林僧相遇的經驗使他相信,在向大自然學習的過程中,不單單只有鑽研個人的禪定技術這樣的課題而已,另一方面他也應該注意,須保持相對應的敏銳度,以便逐一審察在禪定的進程,是否會走入難以挽回的偏鋒。因為意識到自己的任務有多麼巨大,他回到泰國中部多山的區域,獨自隱修於不知名的山洞中。
經過長期在曠野中的精進修行,阿迦曼心裡已經沒有疑惑: 與改革派和傳統派的主張恰好相反,通往涅槃的大門其實尚未完全闔上。正法不在因因相襲的古老傳統之中,也不能在一堆文字中找到,而存在於一顆經過良好訓練的心靈中。文字是修習的指引,就是這樣,不多也不少。關於僧侶的律制,並不只是外在的傳統或儀式而已,它確實在解脫道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修習正法的目的並不是要確認經典文字上的正確。閱讀與思考這些文字,並不足以讓人了解它們真正的涵意---當然也不足以表達對經典的真正尊敬。
如果一個人想要表達對經典真正的尊敬,那麼他必須把修習正法當作一項挑戰:嚴格地檢視那些教誨,並看看它們到底是不是真的。在親身體證這些教導的歷程裡,心將會毫無預期地發現經典文字從未透露的訊息。然而,這些訊息也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檢驗,就在這樣不斷嚐試與修正錯誤的過程中,終將導致最終的覺悟。
這樣修習正法的態度,是與一項古老傳統並行不悖的,而那可稱之為「勇者的智慧(warrior knowledge)」---那淵源於在艱苦環境中開發心智的過程---而那大大有別於「讀書人的智慧(scribe knowledge)」,所謂讀書人的智慧是指人們安適地坐定位,關起門來在書桌上埋頭苦幹而換來的。當然,勇士們在訓練時也需藉助於文字,但只有當這些文字是經過實際體證的,那在他們眼中才稱得上有份量。經典本身贊成了這種態度,如同佛陀教誨他的姨母的一段話,「關於你所知道的教導,『這些教導指引著捨離欲望,而不是擁抱熱烈的渴愛; 要脫離羈絆,而不是被束縛;要去除煩惱,而不要累積它們; 要出離世間,不要與世間糾結不清; 生起堅忍,而不是放逸懶散; 放下重負,而不是又將它們背上。』你應該清楚的掌握住,『 這是法,這是戒律,這是導師(即:佛陀)的教誨。』」
因此,抉擇一項教誨所應依循的最高權威,並不在於這樣的教誨是否存於經典的文字裡,而在於每一個人是不是能以無保留的誠實檢驗正法,並仔細審視這些結果。
當阿迦曼已經親身體證,確認涅槃之道尚未湮滅無跡後,他回到泰國東北告知阿迦索,然後繼續四處雲遊的生活。逐漸地,他得到許多鄉間民眾的歸信。阿迦曼的風範與教誨,深深地烙印在人們的心中;因為這樣的比丘,實在是他們前所未見的。這些人們相信,阿迦曼的一言一行,本身就是正法(Dhamma)與戒律(Vinaya)完美的體現。身為老師,他的教導風格,就有如訓練勇敢的戰士一般嚴格。阿迦曼不以口頭上的教導為足,取而代之的是,他要學生們在艱困的環境裡生存,在那裡致力砥礪自己的心志與人格,並成功掃拭那障蔽心靈的煩惱塵埃;不僅止於教導單一的禪定技術,他也教導他們全副武裝的技巧—就如同他的一位弟子所說的『沖洗痰盂(喻除盡煩惱污垢)的十八般武藝』--然後就把他們送到曠野裡去修習。
差不多在阿迦曼回到東北地區後,第三種型態的泰國佛教在曼谷出現了---現代國教(State Buddhism)---而那也開始衝擊到他的生活。為了要鞏固戰線、一致對抗帝國主義者如英、法等國的威脅,拉瑪五世(1868-1910)要把泰國從鬆散的封建制度,改造成一個實施中央集權的國家。他和兄弟們計劃中的一部份---其中一個就曾當過比丘---就是制定宗教改革法案,以抵制(隨帝國主義入侵的)基督教傳教士。由於當權者受過英式教育,他們把維多利亞時代(已廣泛宣揚)的,所謂「理性」與「實用」的理念,注入僧眾們學習法與戒律的一套標準課程中。舉個例子來說,在一本新版的比丘律典中,他們在傳統型佛教與改革性傳教的立場之間作了一番妥協,意旨在於抵制來自基督教方面的質疑,因為他們說僧侶實在不值得依靠,又過於懶散。另一方面,國家方面要求僧侶放棄他們四處遊歷的生活,然後定居在建好的寺院裡,接受國家統一的僧伽教育。因為法宗派的僧侶在當時的泰國,是受過最高教育的一群人---而且他們跟王室關係一向匪淺---所以,他們為政府所徵募,到遍遠地區從事進一步的工作。
一九二八年,有一位法宗派高階僧侶接掌東北地區的僧務,不過他並不同情於僧人應修習禪定的主張,對那些森林流浪僧也抱持著不以為然的態度。為了要這些阿迦曼的後繼者定居下來,他下令這些僧侶建造寺廟,並要他們協助推廣中央的僧伽計劃。於是阿迦曼與少數幾個學生前往泰國北部,因為那裡尚未明文禁止比丘遊方的生活。在一九三○年早期,有一次,阿迦曼被指派職務,要他在清邁的一間重要寺院擔任住持,不過他在隔天的黎明前就悄悄脫逃了。就在當地掌管僧務的高層一再關切他的修習方式,好說歹說之下,阿迦曼才在非常年老的時候,終於在東北地區定居下來。然而他尚且保留不少自己過去的頭陀行持,一直到一九四九年逝世為止。
在一九五0年代,這由阿迦曼所掀起的一連串運動,還不能得到曼谷當局的接納。一直要到七0年代,此一運動才獲得全國性的注目。這連帶地使現代國教一派立場的比丘頓失光環,而他們之中有不少人,就好比穿上僧服的官僚一樣。最後的結局是,這些森林僧成為法的象徵,在許多僧侶與在家弟子的眼中,他們是佛陀的正法最值得仰賴,也最經得起考驗的真正體現,尤其目睹自己身處於以近似狂熱的步調踏步前進,卻從不稍事停留的現代化變遷之中。
當再次回顧佛教發展的歷史,我們時常會發現森林傳統,有著快速興衰的生命周期。當它失去了原來的動力,就會有其它的發展會順著時勢取而代之。如果我們考慮到最近幾十年來泰國原始叢林所遭受的大規模破壞,也許這將是泰國佛教最後一個森林傳統了。幸運的是,我們西方國家(譯按:作者本身為美國比丘)已即時接觸到此一傳統,所累積的經驗將有助於讓聖者傳統在西方世界的土壤生根,並進一步茁壯成屬於我們自己的森林傳統。也許這些珍貴經驗的核心,將會關係到森林傳統(wilderness)在呼應當代佛教思潮所扮演的地位,(而我們預見)這思潮通常是由城市中的佛教徒們所引領發展的。一直有一種未經嚴格檢驗的說法,以為佛教就是靠著與傳播地本身的文化傳統的緊密結合,所以才能輕易地存續至今,然而經由阿迦曼的森林傳統觀之,難以支持這樣的看法。佛教(Buddhism)本身的發展與正法(Dhamma)的慧命是否久住,兩者並不屬於相同的一件事。像阿迦曼這樣----願意為了正法獻身,以全部的生命探索並親身實踐正法的---才是真正的,使正法長存世間的尊貴之人。當然,人們可以依照他們喜歡的方式,自由地投入任一種佛教傳統,但相信那些受益最多的,將不是那些巴望著佛教能投其所好的一群人,而是願意調整心態,以確定自己能遵循著聖者傳統前進的人們。要找到聖人們的傳統並不容易,尤其當我們考慮到現今不同的佛教傳統之間,已存在著多到令人無所適從的重大歧異,而所造成的混淆實際已延續數世紀之久了。為了確定那一個傳統值得我們追隨,每個人必須回歸本位,發揮徹底、毫不容情的誠實,正直,與洞察力逐一審視。這中間並不存有什麼簡單的保證。也許,這樣的事實本身,就是法的價值的一種體現。只有具備有完全正直人格的,才會真的理解它。一位阿迦曼的學生阿迦李(Ajaan Lee),曾這麼說過:「如果一個人不能完全地誠實面對佛陀的教誨,那麼佛法對他來說,也將不會真實地呈現---當然那樣的人也永遠沒有能力認識到,什麼才是真實的佛法。」
|